弱水河畔古都邑,丝路明珠金张掖。
弱水之滨的文明火种自五千年前已然萌发,这条被《尚书·禹贡》记载为“导弱水至于合黎”的古老河流,见证着张掖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特殊坐标。
甘肃张掖,位于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交汇的河西走廊中部,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的商贾重镇和咽喉要道。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“张国臂掖”的雄浑号令,使其成为控扼丝路的战略要冲;北凉沮渠蒙逊在此建都开创凉州文化盛世;元朝甘肃行省治所的确立,更凸显其西北经略枢纽地位。
文明的馈赠在这里层层累积——东灰山遗址解构“满天星斗”迈向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,山丹军马场延续着两千多年的军马牧养传统,1400多年前焉支山下的“世博会”彰显“混一戎夏”的治理智慧……
让我们走进张掖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撷取其中的若干文化名片,在时空的褶皱里,触摸历史脉搏、感知文明温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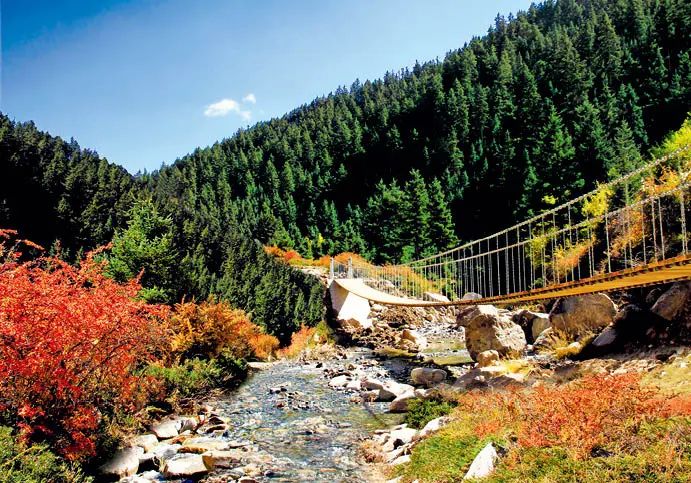
▲焉支山一瞥
东灰山遗址:满天星斗与多元一体
张掖作为中国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,分布着东灰山四坝、壕北滩、红崖子、西城驿、平原堡等诸多新石器时代至夏初的遗址群,其中距今5000多年的东灰山遗址,为解读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提供了关键实证。
考古研究表明,东灰山先民在体质特征上与玉门火烧沟、武威沙井文化群体具有亲缘性,更与中原殷墟中小墓人群存在显著趋同。这种人类学特征揭示出早期河西走廊与中原的交往交流交融,为探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提供了重要线索。
东灰山遗址发现的普通小麦、栽培大麦和高粱遗存,实证了我国旱作农业起源的多元性;其砷铜冶炼技术更是领先世界,展现出卓越的科技创造力。从精神信仰层面考察,该遗址出土的男性石祖和女性白石牝器,既是生殖崇拜的具象表达,更是阴阳观念的原始雏形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,这种具象符号经历史演变,最终升华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哲学理念。
有考古学家作出新石器时代社会同步发展的论断,这在东灰山遗址得到印证。该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说明,在新石器时代,随着包括张掖在内的各地区间交流互动的加强,呈现出文化趋同的发展态势。正如苏秉琦先生“满天星斗”论断所揭示,各地区文化在保持特色的同时,通过技术传播、观念影响形成共同文化基因,最终熔铸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。
山丹军马场:久负盛名的国家马场
山丹大马营草滩,古称“汉阳大草滩”,位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马营盆地,自古为优质牧场,具有数千年的养马史。

夕阳下的山丹马场胡双庆/摄
先秦时期,祁连山地属雍州,山丹大马营草滩为戎羌驻牧地,秦代由西迁的月氏、乌孙等部族占据。汉初匈奴崛起,草滩遂成为匈奴浑邪王治下核心牧区。公元前121年,霍去病发动河西之战,驱匈奴于漠北,部分匈奴部众东迁后逐渐融入中原。这片草滩不仅是丝路文明交汇的见证,更折射出古代游牧与农耕文化碰撞融合的历史进程。
西汉时期,汉武帝设立牧师苑,大马营草滩便成为国家战略马场。西汉马政体系以太仆统辖,下设牧师苑令专司军马繁育,开创冷兵器时代军马供给制度先河。魏晋时期,前凉政权在此设置汉阳县强化马政管理,北魏孝文帝时存栏量突破10万匹,成为京师军马的重要牧场。隋炀帝西巡张掖,诏令在大马营草滩设牧监。唐太宗李世民命太仆张景顺、李思文等经营河西马政,鼎盛时期全国军马七成源于此。
辽宋西夏时期,河西地区仍为养马重镇。明清两代延续官牧制度,清代更因西北边防需求,将甘州大草滩列为战略物资基地。新中国成立后,军马场持续为国防建设输送战马,直至2001年移交中国牧工商集团有限公司,方终结2000余年的军备使命。
作为祁连山北麓水草最丰美的天然牧场,大马营草滩凭借独特地理优势,创造了冷兵器时代单一场域持续育马的超长纪录。其承载的不仅是马种改良、牧养技术的演进史,更是历朝历代中央政府经略西北、保障边疆安全的战略缩影。从青铜马蹄铁到现代种马培育,这片草场见证了中国马政制度从军事驱动到民生转型的完整轨迹,在世界畜牧史上书写了独特的篇章。
北凉故都建康郡:三迁都城与民族融合
五胡十六国时期,卢水胡沮渠氏建立北凉政权。时值后凉龙飞二年(公元397年),沮渠蒙逊兄弟借吕光政权内乱之机,拥立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,改元神玺,定都建康郡(今甘肃省高台县骆驼城古城)。次年迁都张掖,开启北凉经营河西走廊的阶段。
北凉时期,军事上向西拓展至十二郡,控制高昌涉足西域;政治上沿袭中原职官郡县制度,推行汉文化并崇奉佛教。这种治理模式不仅为沮渠氏后续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,更促进了河西走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。
公元401年,沮渠蒙逊政变夺权后,采取灵活对外策略,初期臣服南凉,继而与西凉结盟,集中力量先后击溃后凉与南凉。公元412年迁都姑臧(今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),称“河西王”,标志北凉进入鼎盛期。至公元439年北魏攻占姑臧前,其西控西域、东据河陇,成为河西走廊最具实力的地方政权。后姑臧被北魏攻破,沮渠无讳、沮渠安周在河西酒泉、敦煌短暂坚守,于公元442年将都城迁至高昌,重建大凉政权。
值得一提的是,张掖建都时期(公元398—412年)虽仅有15年,却发挥了关键性历史作用:其一,形成军政制度框架,沮渠氏在此积蓄力量完成由弱转强的蜕变;其二,清除后凉残余势力,为最终定鼎姑臧扫清障碍;其三,通过佛教传播和商贸往来,促进河西走廊胡汉文化深度交融。
北凉政权存续64年间,历经三次迁都(建康—张掖—姑臧—高昌),始终维系着中原与西域的密切往来、和谐交融。尤其在张掖时期实施的中原郡县制,不仅为北魏治理河西走廊提供了范本,更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留下深刻的民族融合印记。
焉支山盛会遗址:中国历史上的首次“世博会”
焉支山位于今张掖市山丹县东南,属祁连山北端支脉,为黑河与石羊河水系的分水岭。自张骞凿空西域,中原与西域往来日盛,西域诸部深受中原文化影响。
隋大业元年(公元605年),隋炀帝派遣裴炬赴张掖主持与西域互市。裴炬广泛搜集西域地理、民俗、物产等资料,撰成三卷《西域图记》(今佚),并向隋炀帝谏言:“越昆仑而跃马,易如反掌”“诸蕃即从,浑、厥可灭”,力陈经略西域之利。
为巩固边疆、畅通丝路,隋炀帝于大业五年(公元609年)亲率大军西巡,经大斗拔谷(今甘肃省民乐县扁都口)抵张掖,随后在焉支山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“万国博览会”,接见西域等城邦27国使臣。博览会上,展陈西域珍宝,上演胡旋舞等。隋炀帝设观风行殿宴款请使臣,将献地首功的伊吾吐屯设、高昌王置于御座之侧,余者列于阶下,通过座次彰显恩威并施的政治智慧。此次西巡,开创了中原王朝君主西巡河西之先例,不仅强化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地方的管辖,更推动丝绸之路贸易进入新高峰。
焉支山博览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这场“宣示国威,怀柔远方”的盛会,通过万国来朝强化了“混一戎夏”的政治整合,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。自西汉设立西域都护府后,中原王朝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断续管辖,至隋焉支山盛会重铸丝绸之路秩序和繁荣,不仅恢复了汉晋边疆治理传统,更为唐代及后世对西域的有效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祁连山北昭武城:丝路纽带中的文明交融
“昭武”系今张掖临泽县旧称,从汉至晋使用近400年,西晋避文帝司马昭讳而改为临泽。据《隋书》《北史》记载,康国乃康居后裔,其王姓温,本为祁连山北昭武城月氏部族,后为匈奴所破西迁葱岭立国。其分支诸国皆冠昭武之姓,以示不忘祖源,史称“昭武九姓”,其名即源于故地昭武城及月氏渊源。
月氏西迁后建立贵霜王朝,公元3世纪后解体形成诸多绿洲邦国,分布于当今中亚的索格底亚那、费尔干纳及巴克特里亚等地区,即中国史籍所载“昭武九姓”诸国。历史研究表明,自两汉至隋唐,月氏后裔始终活跃于河西走廊:汉简中已见张掖地区康、史、安、曹等姓氏记载;两汉之交的张掖太守史苞、酒泉太守竺曾(月氏高僧竺法护支姓族人)皆属月氏系统。
十六国时期,康、史、安、曹、何等粟特化家族以河西大族身份深度参与五凉政权,虽保留有一些中亚习俗印记,但久居河西后不仅在血缘上、更在文化上都与当地人有了充分交融。这些家族始终传承着“祁连山北昭武城”的祖源记忆,将昭武城视为精神象征。
至唐代,昭武九姓群体进一步深入中原,除承担丝路贸易职能外,康、史、安、曹、何、米等姓氏普遍与当地人通婚,进一步实现深度融合。以月氏人的直系后裔“支”姓人群为例,他们从西域迁至河西,再到中原和江南;《支彦墓志》称其是酒泉人,是周大夫伷的后人,旨在表明支姓是华夏之正宗;《支敬伦墓志》《支成墓志》《支谟墓志》等皆记志主爱好儒学、文化修养很深,等等。
在张掖回首往昔,可以清晰地看到粟特商队与河西大族、西域及中亚城邦与中原王朝的双向互动,展示了丝绸之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、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图景。
作者汪晓瑞为甘肃省张掖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,蔺海鲲为河西学院教授
 版权所有:中共张掖市委统战部 陇ICP备13000766号
版权所有:中共张掖市委统战部 陇ICP备13000766号